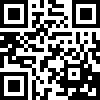云南民族使用的染料以植物性染料最多见,较少用其他染料。这些植物染料有人工栽培的,也有自然生长的。植物染料可利用的部分包括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。这样的染色方法十分落后,效果也不是很好。尽管如此,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区域广阔,生活区域天然资源十分丰富,采集简单,所以利用植物染色的方法,不仅至今具有实用价值,而且它所揭示的印染起源具有民族学的研究意义。据我们调查,云南少数民族使用的植物染料品种繁多,不同民族的喜好、习惯又各有不同,因而对染料的运用也有所差别。

从许多从事旋染的民族来看,少数民族已经充分认识到浸染次数越多颜色越深的道理。大理白族自治州使用旋染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大多数染工认为,旋染八九次时织物上的蓝色最为鲜亮,少于此数则色淡,多于此数则偏深。他们还认为颜色的深浅与浸染技术、染液、晾晒、气候都有一定的关系。在调查中,我们了解到旋染织物还可以利用微生物作催化剂。如利用酒糟等可促进蓝还原,更好地还原染色。嵌蓝与其他染色植物具有很好的配伍性的特点,很多云南的少数民族都有认识和利用。居住在富源县古敢乡的水族,往往要将布染四个蓝后,再添加入倒挂刺树的汁液和猪血,染出的织物黑里透红,经久耐洗,不易褪色。

顾名思义,染具就是入染织物所使用的器具。染具随着染色技术的发展而发展,使用染具使入染织物更方便、快捷,并逐步向专门化发展。在我国,关于染具最早的记录是《秦汉金文录》和《与陶斋吉金录》两本金石书籍收录的“平安侯家染炉”铭文拓片、“史侯家铜染杯”铭文拓片,反映了秦汉时期染具的情形。

虽然已见不到实物,但证明染具在我国出现很早,也表明了印染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。从拓片中提到的染杯的情况来分析,可以知道当时的染具容积不大,估计用来染少量的丝帛,也可推测当时染的规模不很大,但已经具有一定水平。目前,我们对古代染具的情况知之甚少,古代典籍很少提及,有关的出土文物也很罕见。

从印染特点来看,可作如下分析。古代很少使用容易保存的染具(即金属染具),如染锅、染棒等,因为其中含有金属粒子,这些粒子会使织物的颜色出现偏差,色度不易掌握,因此染家一般都不采用金属染具。古代大量采用陶、竹、木等类物质作染具,取材容易,制作简单,对颜色无影响,但易损坏,不易保存,所以出土文物中罕见染具。

云南少数民族至今仍使用大量的陶、竹、木染具,少用金属染具,从中我们也可以推测染具的一些早期情况。据调查,各民族使用的染具主要有以下三种:灶、染缸、染棒。不同民族所使用的灶、缸、棒各有差异。
(1)灶
灶主要是供入染时煮沸之用。家庭小规模入染所采用的灶与炊事兼用,作坊则设有专门的染灶。其形制大致可分为两种,一种是与炊事并用的土灶,或架有三脚架的火塘;另一种是设于作坊的大灶,或设于河边或临水处的临时大灶。

(2)染缸
染缸是染色必不可少的用具。染业行话说“一缸二棒”,就说明了染织业中,染缸和染棒的重要作用。云南少数民族所使用的染缸,从质地大致可以分为三种:
陶质,最多见的是缸、盆,使用的民族很多。会制陶的民族自己烧制,不会制陶的民族购买。使用时,染缸(盆)的大小,决定于入染规模。小的直径大约30厘米,高20厘米;大的直径50-70厘米,高80厘米。

还有木质,此类染缸较大,采用多块木片,以竹箍或铁箍,箍为圆柱形,配上圆底制成。较大的生产单位多使用这种染缸。我们曾对大理白族自治州某生产单位的染缸进行过实测,其高150厘米,直径120厘米,四周搭有方便入染操作的脚手架,供操作者上下,投放、晒晾入染的织物。最后是竹质,若入染量小,小至一缕色线,便没有必要使用大的染缸。景颇族、德昂族、佤族、傈僳族等民族的居住地竹丛遍野,竹子又粗又大。需要入染织物时,只要砍上一段竹子(两端保留节),再砍削成一个长方形的竹槽,槽中盛染液,便可用染棒或以手翻动、拧绞织物染色。